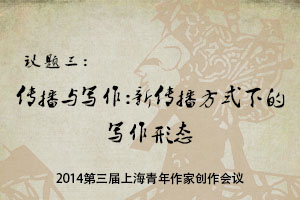开会的时候不由自主、从头到尾、全神贯注的倾听了大家的高论,确实有很多感想,也受到很多启发。我记得德国的顾彬先生曾经对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提出很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开出了"药方"。他很严厉的批评当代中国小说家都不懂外语,我希望顾彬现在能知道我们开了这么多会,在场还是有不少小说家是懂外语的。顾彬先生认为懂外语如此重要,我想我们由此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继续发展的新的希望。
上午谈的是翻译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尽管翻译在我们文化中起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关于翻译理论,和关于翻译一些在我看来是常识性的问题,在公众中乃至于在文化中远远没有得到讨论,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开了一个很高大上的会议,专家们很激烈的批评了我们现在的文学,以及现在的语言,用了大量的外来词、外来概念等等。我有时候还是有荷尔蒙的,那天就荷尔蒙发作,没有忍住,后来我说,您的所有意见我都赞成,但是我也提醒您一句:在你的这一篇发言里,如果把从《佛经》开始的外来词汇全部去掉,你就没法说话了,你的整篇发言就无法成立了,若像思想这样的词,所有都去掉,那就不要讲话了。由此可见对于翻译这件事,尽管我们大家认为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还是如此重要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想的很少,我们谈起翻译只有三个标准--信、达、雅。听上去很顺,"达"是把一个疙瘩的东西给理顺了,然后再"雅",三条全达到了,恐怕真的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我经常感慨:中国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觉,我们总是感觉外国人彬彬有礼,外国人哪怕是黑社会,你踩他一脚,他也会说对不起,外国的农夫和流氓都用书面语说话,其实并非如此,外国人也可以满嘴土话、脏话,这个幻觉是从哪里来的?都是黄昱宁他们给我们制造出来的,因为他们把那样的语言活活变成了那么雅的书面语,反过来,我们觉得外国文明很好,所以说语言创造现实,它就真的创造了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而言需要谈的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还有相应的语言问题。因为今天,在年轻人都在的情况下,我感觉好像没有人谈到语言文化,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谈论文学,包括谈论新媒体时代条件下的文学,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对这些语言、这些问题的警觉和敏感,我们可能只顾着抓那些看上去很高大上的问题,但是语言的问题可能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上海在文学中,我发现文学中上海是没有外省的,在上海文学中,或者像刚才战军所说的传统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外省的维度,一个强大的维度是世界的维度。但是外省的维度很小,幸亏有了知青,都是知青上山下乡才使得上海的作家们意识到还有外省。这个事很有意思,我有时候读30年代上海的文学,当时对上海的描述说那是黄金十年,上海在当时生机勃勃,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读这些的时候,我特别好奇当时的上海是否知道它的未来不是由内在决定的,而是由离它几百公里,不到一千公里的,连它都不屑一看的中国农村发生的事情决定的,我想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意识到。我提这个没有任何结论的问题,只是想说在上海写作意味着什么?在上海写作意味着是高大上的、国际化的、全球的,这个城市的姿势,或者它内在的姿势是不是就包含在背对着的一些东西内,以及这种姿势中的利弊它使我们看清什么,而没有看到什么,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上午我听到了黄平谈到甫跃辉小说中很重要的意向,大象的脚压下来,每个人相对于那个大脚我们都是小众的。某种程度上我们面对庞大的,巨大的,几乎无法掌握的时代,把它作为一个作家的焦虑,在这种焦虑中也让我想起傅雷当年对张爱玲的批评,这个批评对我而言既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是说,他是用一种鹰的标准来要求一只猫,这个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道理的,它本来就不是一只鹰,你问它为什么不是一只鹰,这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傅雷对张爱玲提出的问题,也是对未来的上海作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样一个特殊的方位,它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还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不要辜负和浪费这个位置,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真正看到一些壮阔、宏大、复杂的东西。
今天下午听到很多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表述,发现几乎每个人都用到一个词,叫做个人经验,好多词用起来顺当,但经不住推敲。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我们在讲这个作品很重要,后来文学所的陆所长提到个人体验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教授被他问住了。个人经验是什么意思?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个人经验意味着什么?它在什么样边界上说每个人都有个人经验,什么样的边界下个人经验对小说家如此重要?或者这样的个人经验在小说中的有效性究竟体现在哪里?还是这种个人经验是否真的就像走走面临的问题那样?在我看来,个人经验到底是什么?还是说个人经验变成了一种我们谨小慎微的,或者津津有味的,守着自己的这样一个经验的有限性;或者说守住我们在这样有限的经验中所能够领会到那点意义?而这个近于枯竭的、正在枯竭的、那个有意义的有限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真的值得我们去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小说难道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的个人经验?小说到底是什么,是诗吗?是一个私人日志吗?不是。那是什么?它是虚构。我们作为小说家是否真正想过虚构的力量何在,是否真正的想过人类为什么要发明虚构这件事?所以前几年我在研究虚构问题时,经常有记者向我提问:你是不是对虚构失望了?我回答恰恰不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小说太非虚构,而我们的非虚构又太像小说,就像我们的小说家有时候太像会计,而我们的会计有时候太像小说家。虚构的力量在哪里?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以我们如此有限的经验,而感觉到我们把握不了它的时候,是否真的应该想办法运用这个虚构的力量,虚构就是让你在不可能中去探求和确证那个可能,去开辟那个可能,恰恰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我们想得不够。
刚才听到腾肖澜谈到他写了一个近似于类型化的小说,他通篇带有强烈自我辩解的味道,好像自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辩解一下,为什么要辩解?纯文学这个概念真的包含着伦理,包含着文学全部的真善美吗?还是说我们这些年,特别80年代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这样一种对于小说、对于虚构的一整套观念,包括作家们的自我表达,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造成了虚构精神的瘫痪。我也特别赞成小白在发言中讲到的:我们确实需要在那个时代重新去建构一个,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时代建构一个小说传统,一个真正开放性的,不要在这个建构中非要说纯文学是正确的,是开放性的,充满活力、充满可能性的新的小说传统和小说传统这样的事业。而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最有利、最有效、最有可能的地方在于,如果我们在这张960万平方公里地图上找的话,我一定会找出来,因为我认为上海应该是能够建构起这个东西,并且产生出真正好的作品的地方;在小说艺术上,在小说以虚构去应对这个巨大、庞杂、难以把握的时代,能够在这个方面有所进展的,那么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上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