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1日13:51 来源:思南读书会 作者:思南读书会 点击: 次

从左至右为项静、袁凌、郭爽
撰稿:蔡圣辉
5月18日下午,作家袁凌携新书《我的皮村兄妹》做客思南读书会第456期,与作家郭爽、评论家项静分享他与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交往,感受他们生命中的晦暗与明丽。
超越写作与被写作的关系
《我的皮村兄妹》是对皮村文学小组诸位成员的人生故事展开全景式描绘的非虚构作品。是对当下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整体性书写。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文学的照耀下,于各自的困境中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
活动伊始,项静对皮村文学小组做了简短介绍。皮村文学小组汇聚了许多爱好文学的北漂打工者,他们白天从事不同的工作,晚上聚集在此,在专业写作者的主持下,共同上课、学习,彼此切磋、交流,写下各自的生命故事,皮村文学小组也因此成为如同家一般的地方。

项静
提及创作初衷,袁凌坦言想以第三者的视角为文学小组的成员留下群像式记录,“文学小组的人并不固定,有些人较为资深,已创作多年,还有一些人陆续发表着作品,虽有创作势头,但基本上仍是业余时间创作,更多人将写作视为爱好。这是一个松散的,有流动性的,但也有核心的群体,我想将他们的全体群像保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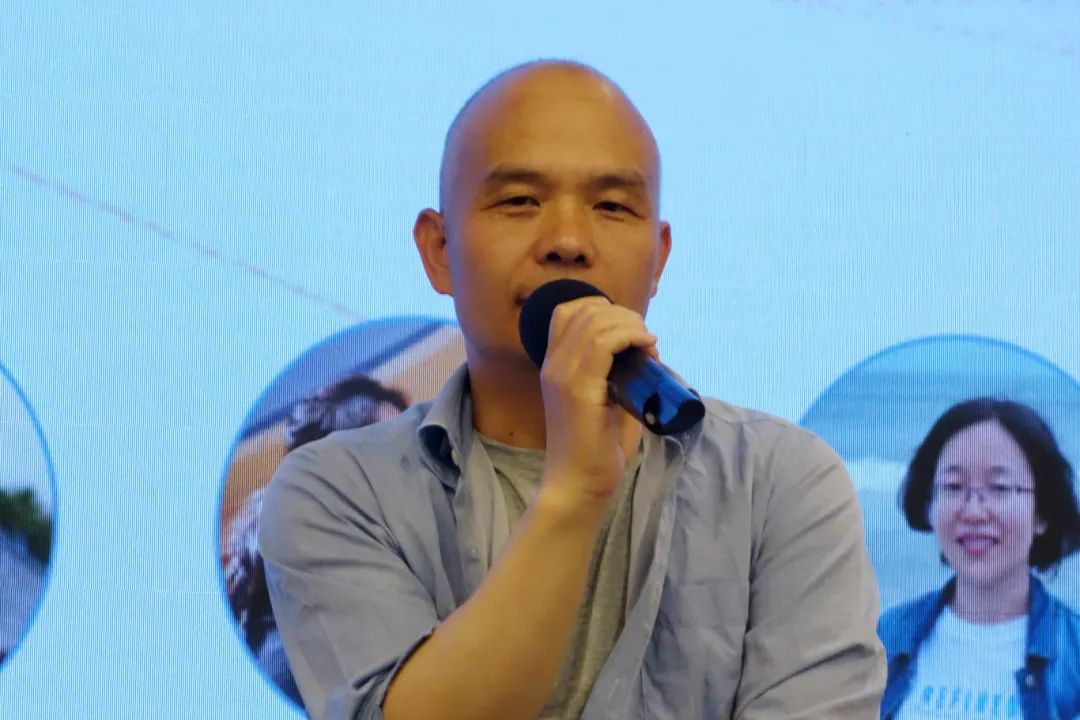
袁凌
郭爽认为,皮村既是一个自然村落,也是一个非自然聚集体。书中描绘的皮村居民并非皮村本村人,他们从其他如皮村一样被边缘化的自然村落中流落而出,去往全国各地打工谋生,而后因共同的精神追求汇聚至皮村,形成了共同体,从而获得了集体的温暖。就此,郭爽向袁凌提问,他与这些看似陌生的群体是如何建立信任,以至于能够互相称为“兄妹”的。

郭爽
袁凌回忆,他身上带有一种粗粝性,在去皮村前曾在北京的城中村生活过两年,因此能很好地融入皮村生活。而文学小组的成员最初将他视为同样去听课的同类,彼此间并无隔阂。相处过程中,双方建立了超越“写作者与被写作者”的密切联系:袁凌与他们共同生活、娱乐,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向袁凌寻求帮助。另外,作为初学写作者,他们还能与袁凌真诚地谈论文学。“虽然我与他们在学历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世界观上并无太大区别。并且非同一圈层的人之间的接触,反而能拓宽对方的生活。我与他们确实有某种感情和交往,这些交往并不会随一本书的结束而结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写这本书并不是利用或冒犯了他们,相反,他们感受到了尊重和自身生活的价值。这也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止于书写与被书写。”
生命的困顿与文学的光
项静注意到了书中男女性的区别。作品的第一部分《相遇》聚焦于四位有共同特质的女性:她们在北京承担着繁重的护理工作,如保姆和月嫂。尽管婚姻生活大都不幸福,但受制于社会舆论或孩子等因素,她们并没有选择离婚。相比起“女性觉醒”的故事,她们的生活底色更多是承受与沉默。承受之余,她们进行创作和表达,但文学并没有让她们放弃生计问题。相比之下,小海、万华山等男性的生命形态则更为自由奔放,但这恰恰也构成了令人困惑的问题。当女性维持着较为可观的收入时,他们却在获得一定的工资后便不再干活,继续创作。他们如同堂吉诃德一类的文学人物,即使仅拥有破战车也要不断冲锋陷阵。由此,项静追问,皮村文学小组对这一群体而言是怎样的存在?是为他们提供了精神表达的空间,还是让他们孤注一掷地追寻文学上的“成功”。

现场读者
袁凌回应,总体而言,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都没有脱离劳动者的身份。一方面,他们仍在承担生活加诸于他们的重量,另一方面,他们保持文学的爱好。正因如此,文学于他们而言仍是一种原初的梦,也因此显得格外质朴动人。史鱼琴曾罹患乳腺癌,而后做手术切除双乳。有天在上文学课的路上,她产生错觉,误以为癌症复发。短暂的绝望后,她认为即使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今天也应该听听文学课。之后她仍然一边上课,一边从事月嫂工作。小海与万华山也并没有因创作而放弃劳动,“他们首先立足于劳动活着,其次把文学作为生命中的光辉,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现场读者
在郭爽看来,文学为小海提供了慰藉。书中提到,小海最初接触文学是在梅山岛打工时,在镇上的大润发超市看到一本《唐诗宋词元曲》,小海决定买下,自此“打开了诗歌的世界”,“恢复了被工业病麻木掉的感觉”。文学为小海提供了精神出口,在工厂做工之余,他会吟诵古诗,也会利用废纸片创作诗歌。此外,文学也为他带来了审美教育,让他重新发现身边的世界,懂得欣赏自然之美。“文学无缝不入地渗透到他生活当中,给予他巨大的能量回馈,从而消解部分困苦,让他的生命充满热度。”
晦暗以外的明朗色彩
项静谈到,作品像一本人物志,其中每个人物都与他人缠绕交织。他们的背后是广阔的中国社会,包括他们在乡村中的生存处境以及与周围人的交往。这些故事丰富了项静对这类人的了解,她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苦难之外的更多色彩。如身为泥瓦匠的徐良园不仅实现了物质上的安稳,也靠性格上的自律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精神上的富足也可以看做另一种维度上的成功。“范雨素曾表达对中国文艺的不满,现有的文学与影视作品的打工人形象单一。他们希望自己向大众还原他们的世界的本来面貌。袁凌的写作剥除了很多他们身上烙下的刻板印象。”

读者提问
袁凌补充,他所熟识的徐良园始终没有失去格调与尊严,如洗澡前先将水晒热、将门头改造成电动车能够出入的缓坡。袁凌坦言,皮村文学小组的许多成员都如徐良园般保持着超出他既往认知的风骨。譬如史鱼琴涉猎广泛,掌握“采薪之忧”这样的生涩词汇,在读书过程中也能注意到常人忽略的细节。因为她有自身独特的审美和注意力,对于知识既不笼统崇拜,也不生吞活剥。小海身上亦有过人的坚韧性,即使在困窘中已度过近四十年,但仍能随时调动自己的能量。
郭爽认为,出于性别限制,相较于对巧珍等女性的书写,袁凌对小海的描摹更为立体。由此,郭爽提出一种可能性,若袁凌能更深入地进入到巧珍等人的生命内部,观察到巧珍在地下舞蹈室中释放的能量、她与姐妹在一起时的热情与互动、她对这个世界隐秘而细微的渴望,将会形成更丰盈的文本。

嘉宾为读者签名
袁凌表示同意,并提到在写作过程中,为克服单视角叙述带来的主观性,他尽可能将人物放置在与他人的互动与交叉中描写,并且不将人物树立成完美的弱者形象。“书中的许多人具有喜剧性和悲剧感的极致张力。他们以自身的承担和能量消解了我们产生的悲悯之情,呈现出更多明朗的色彩。虽然生活很沉重,但他们有自己的主体性,并非完全被生活碾压。这是比纯粹展示生命中的悲怆更值得尊敬的,也是我想要书写他们的原因。”袁凌如是说。
思南读书会NO.456
现场:戚译心
直播:张师恒
撰稿:蔡圣辉
改稿:郭 浏
摄影:迟 惠
编辑:邹应菊